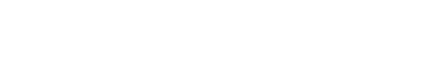时间开始的地方
薄学斌
冬天是适宜追念的季节,万物清平,树木枝柯简洁,记忆也似乎更加明晰。至于“萧瑟”二字,到这个年纪已不在感怀之列。百炼成钢,其实就是砍削、打磨自己,让一个人看起来方正、持重、有力。不再为时间焦灼,把它熨平,变得宽大、自在、可塑,几能绕指柔。时间相对于空间来说,无始无终,永不驻留。相对于个体或某个群体来说,是光阴,是岁月。那么,我和母校的时间是从何处开始的呢?
当然是1986年的夏天,正在老家山中放牛,弟弟跑上来叫我回去,说是大学录取通知书到了。按高中时的成绩,考上大学还是蛮有信心。因为家在豫鄂交界处,志愿中的学校都在武汉,甚至早已暗自筹划报到的路径。
看到信封时,着实吃了一惊,校名是“河南师范大学”,我并没有填报过,疑心是搞错了。打开看,的确是我的名字,录取到“教育系教育管理专业”。“教育系”是教什么的?这三个字我只在课文《记念刘和珍君》关于“程君”的注释中看到过一回。“教育管理专业”将来要干什么、能干什么?第一反应是泄气、抵触,打主意复读。父亲看着我,良久,说:“怎么不是个商品粮?”
夫复何求!我就这样被轻易说服了。然后是漫长的报到旅程:先是过四次河,到乡政府所在地,赶早上那趟往县城的班车,无座。接着从县汽车站搭下午的班车到信阳火车站,有座。乘火车——后半生我一再回忆的绿皮火车,去新乡,6个小时,站票。凌晨到达新乡火车站,找到迎新的牌子,随之上了一辆大卡车。夜风浩荡,除了时不时低头躲一下树枝,什么也没看清,就被带到一小片空地——后来知道那是两排宿舍楼的中间地带。一个大高个接上我,看了我的通知书,示意跟他走。双腿僵硬,昏昏沉沉,上楼,进房间,他帮我把行李放在门口左侧的上铺,我知道,这就算到了。一路风尘仆仆,想洗个澡,就问他哪里有水?说了几次,他怔怔地看着我:“你写下来好吗?”于是我写了一个“水”字,他大笑:“这是shui,不是sei!”好吧。他叫吴生义,不是高年级同学,更不是老师,是我同班同宿舍的新生,也是第一任班长。
迷迷糊糊睡了一觉,醒来已是上午10点多,草草洗漱,没吃早饭,一是有点感冒,二是不知道食堂在哪里。按照提示,下楼去买日用品,发现竟像农村的集市,脸盆、毛巾、肥皂、热水瓶、席苫之类的,沿着宿舍区中间的那条路摆成长蛇阵。拎起几件东西,跟着走进1号食堂——比我们中学的操场还大,从西向东十几个高阔窗户,每个窗下两个小窗口。看了一遍,因身体不适,没有一个想吃的。但不吃肯定扛不住,就又看了一遍,发现“卤面”。想当然地认为是老家卤肉汤煮的面条,应当好吃,要了一份——从此在豫北三十多年,拒否那种又干又硬、酱油上色、少油寡味的蒸面条,虽然后来我知道在当地是重要主食,而且家家户户各有妙招,逢年过节或贵客登门才会上桌,但于我已是杯弓蛇影。
然后是军训,漫长的军训。有两个教官,其中一个稍矮、壮实,在我们队列前示范匍匐前进,朝一个小水坑径直爬过,让少男少女惊呼一片。整天立正、稍息,正步、跑步,瞄准、射击。还有军事课,至今记得“三三制战术”。教官与学生结下深厚友情,临别时几位女同学泣下沾襟,仿佛将会有故事发生。
同学就这样慢慢熟悉了。第一学期每天一大早集体跑步,大家轮流执勤喊操。有一天我站在队前:“向右——Juan,跑步——走!”一阵哄笑,正莫名其妙时,赵燃突然折回来冲我做个鬼脸:“向右juan——”哦哦,原来他们把这个字念“zhuan”……
那时穷孩子多,不管来自城市还是农村,手头都紧得很,学校鼓励勤工俭学,就是让大家各显神通挣钱自己花。比如,李为忠从烟厂搞来次品烟卷,用一个大塑料袋装着,挨寝室兜售,自然比较难卖,就自己抽,但因过滤嘴粘接不好,一吸四处跑烟。还有两位女同学,在西二楼东边卖面包,紧邻一个烧饼摊。烧饼葱香,芝麻也多,长条状,我们叫它“鞋底子”。这“鞋底子”实在太好吃了,大家竟不顾同学之情,忽略那些面包而直奔泥糊的缸炉……。她们有时拿起面包送给同学,人家肯定不能要,就前面跑,后面追。当然,不是所有同学都具有商品意识,比如个子不高,成绩很好,走路很快,鞋跟恨不得把走廊楼板蹬塌,身体扭得要撞墙的宋晔;个子同样不高,成绩更好,毒舌善辩,骑着斜杠自行车到处蹿的王红;还有诳我一起到某女同学家吃茶叶蛋、现在时常表现稳如老狗的张全胜,趣事很多,考虑他正含饴弄孙,按下不表;还有同一宿舍的冯建军,上大学时就在省级以上专业期刊发表十几篇论文,搞得编辑来信,抬头竟是“老冯……”。某个晚上,熄灯后大家正在酝酿入梦,他突然说:“祝爱武跟我散步老说自己冷得慌,是啥意思?”
我爱同学,更爱吾师,而且敬爱每一位老师,不管是教专业课还是公修课。专业课很多,教育学、教育管理学、教育行政学、教育经济学、学校后勤学、学校卫生学……一个头两个大!记得教实验心理学的华克伦老师用一种仪器把一截铁丝从高处垂直坠下,要我们伸手握住,然后给出一个分值——依然记得个个煞有介事的表情!喜欢解剖生理学赵晓进老师、哲学司小莉老师、逻辑学谢根成老师、大学语文王文彦老师,但大学英语张志伟老师的发音与我完全不同——我可是民办教师调教出来的“种子选手”啊!还有87级辅导员邓铸老师,住在隔壁,某年冬至,我和同学把他的煤火炉搬去煮饺子,他一声不响,拖家带口上街买饭吃。还有宋鲁伟老师,明明是89级辅导员,偏偏喜欢混迹于86级学生中间。某天结伴到黄河故道野炊,有人挥舞菜刀劈砍树枝生火,他刚夸赞何其英武能干,发现竟是自家菜刀,顿时心疼得咬牙切齿。除了老师,还有中一楼西墙下的鞋匠,好像是师大子弟,精瘦,嘴勤,手快。媳妇相当富态,中午过来送饭,坐在一边安静地看他干活。每个假期前,我们都到他们那儿拿粮票换路费。那时买粮食须有粮票,他媳妇是农村户口,学生假期回家又用不着粮票,这生意自然好做。
说到这里,估计谁都能看出我不是一个好学生。尽管所有老师对我关爱有加,但自己实在算不上对本专业抱有浓厚兴趣,各科成绩差强人意。庆幸母校有一座条件较好的图书馆,让我有机会读完中学历史课本中所有标出书名的中外名著——从农村高中考上大学,文学与文化的视野极其有限,我以为历史课本开列的书,一定是最好的。读完这些书之后,就到图书馆一楼东侧的开架书库,像进超市一样选书、借书,碰上什么读什么,喜欢什么读什么,甚至因为一个特别的书名就填表借阅。读得很杂,其中文学和哲学相对较多,从鲁迅、胡适、郭沫若、徐志摩、沈从文、林语堂到艾青、李季、张洁、路遥再到所谓的“新生代”,从余光中、洛夫、痖弦到艾略特、惠特曼、海明威、罗曼·罗兰、陀思妥耶夫斯基,又回过头来读《诗经》《楚辞》等等。听说文学是要有思想的,于是又从叔本华、萨特、伍尔夫到海德格尔、帕斯卡尔,再回头读《老子》《论语》《庄子》等等。当时的知识结构其实是难以容纳和消化人类文明史上的诸多煌煌巨著的,因而不少篇章看得很粗疏,尤其是那些“汉译名著”,舶来的语言习惯和思维方式成了囫囵吞枣的理由。
如果说还有点收获的话,那就是很早不再去思考类似“我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的深刻得愚蠢的问题。不管发生什么事情,面对就是了;不管接到什么任务,学习就是了。参加工作越久,岗位调整越多,离原来的专业就越远。时代变化加速,社会变革加剧,新问题新挑战新压力层出不穷,甚至每天都要面对前所未见的困难和局势,这需要团结很多人一起努力,也需要认认真真潜心学习。在母校的这一段经历,让我对知识具有敬畏之心,尊重科学,尊重规律,尊重创新创造,但从不畏惧新事物,不囿于原有的知识结构,不因保守而自我原谅,敢于否定自己、打破自我,尽最大可能适应新环境新条件新使命——突然觉得词不达意了。也许,我只是想告诉学弟学妹们,从来没有什么诗和远方,只有脚下的路。专业课真的很重要,是安身立命之本,不要像我那样浮皮潦草,毕业后到中师任教,较长一段时间手忙脚乱。同时,更重要的是学习能力,人生很长,大学里学到的知识不过杯水车薪,如不及时更新、拓展,理念和方法都只会刻舟求剑。要善于自学,抱着极大的热情学习专业课之外的知识,不要考虑是否有用,能读多少读多少,有多远走多远,因为永远不知道明天会面对什么。虽然一时不清楚需要用上哪些知识、哪种能力,但学习能力永远是第一能力。我之所以终于没有成为理想中的自己,就是因为这一能力总是处于失血状态。殷鉴不远,后生努力!
也不知道自己当初不情不愿跨入校门,最后因何又无限缱绻地告别。好像一进一出之间,脱胎换骨,师大已赋予新的机能和机理,成为全部命运的起点和逻辑。大学生活那么漫长,又那么仓促,还没准备好,就毕业了。至今记得各奔东西的那天上午,校门口1路公交车旁边围满了人,车门一开,纷纷挥手,车门一关,哭声一片。我决绝地转身,实在承受不了那样一种分袂。后来一生中经历无数次告别,甚至是生离死别,都没有那一次清晰,没有那样撕裂般的疼痛。我们从此开始一步步达成各自的生命价值。人就像植物一样,有的花朵无比绚丽,比如牡丹、玫瑰,果实已不重要;有的果实十分可贵,比如水稻、小麦,花朵常常被遗忘。但它们毕竟有值得被人珍视和牢记的东西,更多的就是那山野里的草,跟随季节生长、寂灭。我是什么?坚信有自己的、些许与众不同的花朵和果实,但根是草根,不论长多高,不论是香蒲科还是禾本科。生为野草可能是与生俱来的悲哀,也可能是无比伦比的优势,我们有极强的生命力,随处生根,随遇而安,随意本色。
写到这里,已近岁末,四季即将重新流转。回望半生轨迹,很多事情仿佛本来就应如此,早一点晚一点、往左转往右转都不行,但无论怎样,河南师范大学教育系,都是我的时间真正开始的地方。
校友简介

薄学斌,教育学部1986级校友,系河南师大潮兴文学社社刊首任主编。中国作家协会会员,曾获人民文学奖、钟山文学奖等。现任河南钢铁集团党委书记、董事长。
(转自河南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官方微信公众号)
整理人 | : | 张亚婷 曹雪莹 |
责 编 | : | 冯 莉 |
审 核 | : | 孙伟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