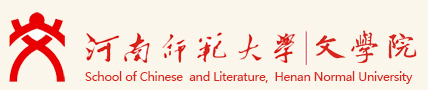针 线
作者:梁小静
终于,我也做起针线来了。
做针线,并不是什么可耻的事情。做针线的时候,可以找出想看而很久没看的电影,ipad在放它的电影,你在做针线。也可以找肥皂剧来看,到哪里不想看了,就停下里,专一地做针线。
做针线的时候,很容易仔细地想一些事情。
前两天,我和朋友说,真想去当裁缝啊。再早一些,我在微信上和黄琼聊天,说我想当个农民,专门的果农也行,就只种苹果。我和黄琼很久没见了。她在江左,我在新乡。我们上一次见面,一起去彭婆乡的山上。到山上的墓园外,下了暴雨,向威的鞋湿透了,他在墓园外一个积雨刚形成的水洼里,洗了脚,袜子搭在台阶旁一棵很硬的藜草上。我记得台阶上是范仲淹的塑像,三四米高,在那个位置,他的眼睛应该是望着群山。我们谁也没有多余的袜子,他就光脚穿上鞋,我们一起在暴雨里看了范仲淹的墓。墓园旁边是长方形院子形成的祠堂,共有两进。一个妇女立在第一进的门檐下,门檐很窄,是瓦片苫起来的。她没有打伞,雨滴入她衣服。她说她是范仲淹的后人,第几代我记不得了。还说她在义务管理墓园,我们交了管理费。第二进庭院偏左的地面上,一株桃树的密枝擦着人的头,桃叶上的水顺着流在人的脖颈上。桃子结得很稠,都长红了,地上又落了许多。急促的雨水把枝条上的桃果冲得很干净。地面上铺着小块的长方形的砖,靠墙的地方长了苔藓,很滑。我从地上捡了桃子,有一股和小院一致的香火味道。
回来路上,天气放晴,车又接着上山、下山。在那几十分钟内,我和山、丘陵离得很近。远处乌青色的连山,和近处红褐色的丘陵,仿佛液体从眼睛直接灌注到我心里。直到那一刻,我才明了心里长久郁结的对山和丘陵的渴念。八月份的草本植物,在雨后绿得透明,它们密集地挨着,不高不矮连成茸绿的一片。我们就这样带着深刻的满足和甜蜜,在山下的一个集市分开了。
今天是新年第一天,早上起来,不知道为什么,我在家里很兴奋,就是一个人的兴奋。想来想去,觉得这种难得的兴奋应该传染出去。我给黄琼发了信息,祝愿她新年里身体更好。因为前段时间她身体不很好。到了十点多钟,她给我回信息。这时我的兴奋劲儿几乎消散了,我在看书,还很认真。她说:我在江左睡懒觉呢。我忽然对这个场景很着迷。洛阳乡下有许多散发这种古意的村镇名字,也有许多像她这样朴素本分、有技艺的年轻人。很多我还不知道。在江左睡懒觉,比在家里睡懒觉要好。
不过,黄琼家里也很好。她家在一个叫凉水泉的地方。小时候爸爸带我去过,我记住了。爸爸骑着自行车,我坐在前梁上。上坡的时候他推着车,我还坐在车上。几岁我却不记得了,但生的肿痄腮的病,还记得清楚。在凉水泉没有看好病,又去了别的地方,是苏家嘴。这种病,就是腮腺炎,曼德尔施塔姆在诗中说吃鱼肝油好了。可是我那时候不知道鱼肝油。我小时候,还常害沙眼。现在想想,是不讲卫生导致的。可是不讲卫生的人很多,许多人却一辈子很健康,我很奇怪。得了沙眼,吃了很多药,都没有好。初三的时候,我的一位很好的班主任,允许我上课闭着眼睛听课。我很感激他。眼睛里从上到下淤满红血丝,这样的眼睛睁开是有点骇人,闭着更合适一些。最后是扎针灸好了,扎针灸的时候是我一个人,从学校请假出去,侧躺在一张临门的医用床上,门外是镇上唯一一条沥青街道。针在耳后扎进去。后来眼睛逐渐变清,眼白也白了。拉开下眼睑,也不再通红,变成正常的浅粉色了。
黄琼也是针灸医生,一双手很瘦很白,虽然很年轻,但一看就知道是医生的妙手。我很羡慕她。她从洛阳下乡,去江左,她以前的病人开车跟到江左,让她在江左扎针。江左真是一个好地方,什么事情都可能发生,有无限的可能性。
黄琼的爸爸对树、菜、枝条的果实,对刚满月的狗、啃草的羊这些小动物都很亲。有一次我去她家,是五月份,樱桃紫红的时候。黄琼妈妈带着我们,给我们摘最甜的樱桃吃。第二天,她爸爸不上班,也到地里来了。他绕着樱桃树,一棵棵地转着看。后来他在一处停下,说这一棵不甜,到秋天砍掉,重栽上好品种。黄琼说,他一点点酸也受不了。他对甜本身的忠实,他对待具体的事物,像对待一种理念和信仰那样严格,想到这些我就很尊敬他。我忽然觉得,无论如何,这样去做一个农人,也会有许多东西可以久久琢磨,最终形成一种生命结构,构成一种有价值的人格。上个月,从微信视频里,黄琼发来一条小黑狗。看起来刚满月,带着胎肥。他爸爸就蹲在小狗旁边看,他吃饭时,要去看看小狗,看看给它的鸡蛋液喝下去没有,喝完了再给它打一枚。可能鸡蛋现在已经不是很珍贵的东西,一只小狗一天喝走几个鸡蛋也不算什么,但他那样凝视抽象一般专注地看,却吸引了人。一只小狗身上,可看的东西是有限的、有尽头的,但他却能够没完没了、仿佛看到了有大意义的无穷尽,这是一种能力。黄琼说,在他更年轻的时候,还看过羊,只是看羊吃草,非常满足地看,天黑了还能看。年轻的时候,这是一种天赋吧。
我也想做这样的农民。在什么时候呢,我不知道。前几天和一个朋友说,想去当裁缝,这很像更早的时候,对另一个朋友说,想去画画。当裁缝,学画画,当农民,都不是容易的事情。说裁缝的事情时,朋友就在家里,当时我在厨房切菠萝。冬天的菠萝,黄脆得仍然像盛夏时那样鲜明。一只很大的菠萝,在透明的袋子里,朋友提着它走了过来,我这样想着,切开了一半,一块块放在白碗里,很耀眼,盐水泡着它,香气在屋里的某个高度跑动着。我记得我返回客厅,又拿起针线。朋友到之前,我关掉了洗衣机。这时候它安安静静的,虽然衣服还在烘干桶里,但丝毫没有妨碍到我们。我缝着,朋友在茶几上填写东西,最后她决定,在表格的某一栏写两首诗。她又给我讲了一次会议中,另外两首诗的事情。这时候,盐水让菠萝更甜了,她说,你歇一歇,一块吃菠萝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