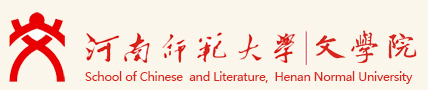东野诗中的力
钟婷婷
孟郊,字东野。
他一身瘦弱,一贫彻骨,一生未曾舒展。写的诗被以一个“寒”字概括,写诗的方式被称为苦思苦吟,人们说他的诗“读之使人不欢”,但又都认为诗中不能没有他这一风格。
总之,他寒弱,又令人惊奇。
一
我惊奇于他写物与用字的力度。虽然这“力”不是昂扬的、光亮的,也不是刚健的、胜利的,而常常是用以书写孤怨的。
他喜欢用锋利的字眼,如“情如刀剑伤”(《下第》),“老骨惧秋月,秋月刀剑棱”(《秋怀》其六),“峡棱剸日月,日月多摧辉”(《峡哀》),“冷箭何处来,棘针风骚骚”(《寒地百姓吟》);再如“一尺月透户,仡栗如剑飞。老骨坐亦惊,病力所尚微”(《秋怀》其三),写一道明亮的月光从门缝照射进来,像一把迅疾的利剑飞至眼前,惊吓了病弱的诗人。锋利的不只有物,还有诗人的身体。诗人体会着自己薄瘦的病躯,说“病骨可剸物”(《秋怀》其五),“剸”就是割,多么特异的对于身体的联想。诗人还用自己的骨头来写寒凉的秋风,说“冷露滴梦破,峭风梳骨寒”(《秋怀》其二),他的瘦骨头成为一把可以栉风的梳子,一根一根的稀疏可辨的肋骨,如在目前。又是写骨头,他说,深秋太冷了,“霜气入病骨,老人身生冰”(《秋怀》其十三)。
孟郊太用力了,不论是选词酌字,还是书写自身,甚至会令一些读者感到不适。关于他用字的锋利,欣赏他的韩愈体会很深,并仿其用字风格,描述为:“刿目怵心,刃迎缕解,钩章棘句,掐擢胃肾”(《贞曜先生墓志铭》),是的,阅读感受正是如此。
除了锋利的字眼,他还喜欢用强力度的动词。如“岁箭迸如雠”(《冬日》),时光携着年岁飞逝,像迸射一般,仇敌一样冷酷地离人而去;如“一纸乡书泪滴穿”,思乡的眼泪是平常的,所以要给它滴穿纸张的力量。写身体经验,则“瘦坐形欲折,晚饥心将崩”(《秋怀》其十三),骨头枯瘦快要折断,饥饿感要把心脏崩裂;写景写物,则“商山风雪壮”《商州客舍》,“朔雪寒断指,朔风劲裂冰”(《羽林行》),“积雨飞作风,惊龙喷为波”(《泛黄河》)……他似乎尤喜“断、射、裂、迸、喷、飞”等爆发式的动作。
此外,令人印象深刻的力量型意象还有风中的旗面,其《京山行》写道:“众虻聚病马,流血不得行。后路起夜色,前山闻虎声。此时游子心,百尺风中旌。”在百尺高处,风一定是强劲的,如此强劲的风所吹动的旗子,令人想象其紧张的、如撕扯一般的状态,仿佛要到达一个无法呼吸的临界点。
二
孟郊诗中的力量,古人也有感受。清代胡寿芝说:“东野清峭、意新、音脆,最不凡,亦少疲薾语。乌得以‘寒’概之!”(《东目馆诗见》)孟郊的好友张籍说他“纯诚发新文,独有金石声”(张籍《赠别孟郊》)。最懂孟郊也很崇拜孟郊的韩愈,说他“受材实雄骜”、“横空盘硬语”、“奋猛卷海潦”,还曾表达想要跟随孟郊一起驰骋的愿望:“低头拜东野,愿得终始如駏蛰。东野不回头,有如寸莲撞矩钟。吾愿身为云,东野变为龙,四方上下逐东野”(韩愈《醉留东野》),虽是醉话,但韩愈对孟郊的赏爱和学习是可征的。对此,宋代严羽很不解,说,“孟郊之诗,憔悴枯槁,其气局促不伸,退之许之如此,何邪?”
严羽只说对了一半,确实,孟郊的所有诗作一起描摹出了一幅愁怨、瘦弱、穷蹙的自画像,但是,他诗中也有狂、也有大,更有生命的力。春天,他写植物生长的力:“雨滴草芽出,一日长一日”,在这自然的生命力面前,他说“且持酒满杯,狂歌狂笑来。”(《春日有感》)在沉浸于诗歌创作时,他说:“天地入胸臆,吁嗟生风雷。文章得其微,物象由我裁”(《赠郑夫子鲂》),他把天地放在心怀里,自信能够摹写甚至创造万象。
他虽寒弱,但说“饿马骨亦耸”(《出东门》)。他虽是一把瘦骨,却以骨自许,曾写“诗骨耸东野,诗涛涌退之。”(孟郊《戏赠无本》)
其实,常被以“寒”字概言的孟郊诗,其中也有火焰的温度。他以火写蔷薇花的艳,“忽惊红琉璃,千艳万艳开。佛火不烧物,净香空徘徊”(《溧阳唐兴寺观蔷薇花,同诸公饯陈明府》);写火热的春色,“春色烧肌肤,时餐苦咽喉”(《卧病》);写寒冬挨冻的百姓想化为飞蛾扑向富人家的火光,“寒者愿为蛾,烧死彼华膏”(《寒地百姓吟》);写学识之于人的启示如同火花,“击石乃有火,不击元无烟”(《劝学》);写不改其性的正直之人,“良玉烧不热,直竹文不颇”(《君子勿郁郁士有谤毁者作诗以赠之》)。这反复使用的“烧”字,是苦寒的诗人在弥补生命缺失的热度么?
他以秋虫自比,并常将自己的衰老体验投射到鸣虫身上,比如“幽幽草根虫,生意与我微”(《秋怀》其四),“秋深月清苦,虫老声粗疏”(《秋怀》其九)。苏轼曾无奈地感慨:“何苦将两耳,听此寒虫号?”(《读孟郊诗》)虽是恨其哀怨不止,却也读懂了孟郊笔下“寒虫”的自喻。
正是因为这秋夜寒虫的代入感,孟郊才有了发现细微声音的一种独特本领。孟郊是喜欢写声音的,尤其是寂静中常人不易察觉的音响,如“斗蚁甚细微,病闻亦清聆”(《老恨》),“幽竹啸鬼神”(《秋怀》其十),“竹风相戛语,幽闺暗中闻”(《秋怀》其五)。或如:“老虫干铁鸣,惊兽孤玉咆”(《秋怀》其十二),诗人用干铁刮擦的声响来形容秋虫摩擦翅膀发出的鸣音,无意中造成了以“联觉”之法增强读者心理冲击的效果。再如,“百虫笑秋律,清削月夜闻”(《奉报翰林张舍人见遗之诗》),东野说他听到秋虫的笑声,这并非超现实写法,失眠掉进过寂静中的人会懂。也是在一个清凉的秋夜,我听到单元楼下几只蛐蛐咯咯复咯咯的笑声,波浪一样,随夜气起伏。亦如在夏夜的深处,清醒的人会听到邻居空调外挂机的运转声,远处的滴水声,还有小区枝头的小鸟的梦呓……
三
认识到孟郊诗歌奇异之处的清代方南堂,说孟郊的部分诗作“运思刻,取径窄,用笔别,修词洁,不一到眼,何由知诗中有如此境界耶?”(《辍锻录》)是的,孟郊诗自有独特境界。我所理解和欣赏的孟郊诗境,便是以寒弱之身,反差式地呈现强烈的生命力量。
孟郊的“气狭”,他自己很清楚,亦多有论者。其诗中有:“尽说青云路,有足皆可至。我马亦四蹄,出门似无地”(《长安旅情》),“出门即有碍,谁谓天地宽”(《赠崔纯亮》),“少年出门将诉谁?川无梁兮路无岐”(《出门行》),“人间少平地,森耸山岳多。折辀不在道,覆舟不在河”(《君子勿郁郁士有谤毁者作诗以赠之》),“吾欲进孤舟,三峡水不平。吾欲载车马,太行路峥嵘”(《感兴》)。他甚至思考总结了各人天生的气性差异,道:“天地唯一气,用之自偏颇。忧人成苦吟,达士为高歌”(《送别崔寅亮下第》)。但天性的“忧”,和气格的“狭”,并未减损他笔下的力。他说,“鸟声有悲欢,我爱口流血”(《苦寒吟》),他就是要做一只啼血的杜鹃,用力地写诗,一首首,寒苦又瘦硬。
借《苦闷的象征》一书中的理论来说,生命之力受到压抑越强,其转化的文艺创造力越强。厨川白村以人和侵入体内细菌的战争为喻,来说生命之力,“这战争成为病而发现的时候,体温就异常之升腾而发热。正像这一样,动弹不止的生命力受了压抑和强制的状态,是苦闷,而于此也生热。热是对于压抑的反应作用;是对于action的reaction。所以生命力愈强,便比照着那强,愈盛,便比照着那盛,这热度也愈高”(厨川白村:《苦闷的象征》,鲁迅译)。而这“热度”是可以化入文艺创作中的,我赞同这一看法。这现实阻力带来的“热度”反映到孟郊文学创作上,才成为李肇所概括的“矫激”风格。
常常,文学创作是个体在现实处境中释放紧张感、压抑感以达到能量平衡的艺术性途径,它为遭遇挫折或拘囿的人们提供了思想传达与情感宣泄的渠道,或一个退归自我的文艺空间。在现实生活中,越有力的内心感受到的压制或束缚越深,当其生命力受到不可克服的阻碍时,便借助文学想象,给予精神以超现实的寄托,并达到不平衡能量的转化或消解。苦闷经验带来的生命阻滞感越强,其文字力度越强。这一点,除了孟郊之外,中唐的李贺、卢仝和法国的波德莱尔、兰波等诗人及其作品皆可为例证。
晚唐陆龟蒙曾有文曰:“天之赋才之盛者,早不得用于世,则伏而不舒,熏蒸沉酣,日进其道,权挤势夺,卒不胜其阨。号呼呶拏,发越赴诉,然后大奇出于文采,天下指之为怪民。呜呼!木病而后怪,不怪不能图其真;文病而后奇,不奇不能骇于俗,非始不幸而终幸者耶?”(陆龟蒙《甫里先生文集》)
一生贫寒而拘挛的孟郊,在诗歌创作中,勇猛地突破“温柔敦厚”的诗教传统,枯手执笔,释放着文字的创造力,更传达着生命的强力。
古今诗歌能够触动读者之处,或在情(感),或在(哲)理,或在美。美有万种,力量感,便是其一。
最后,借两句诗送给孟郊:
“一匹马站在阴影里,四蹄深陷寂静
而血管里仍是火在奔跑”
——沈苇《林中》
——记于2021年6月。
(钟婷婷:文学院教师)